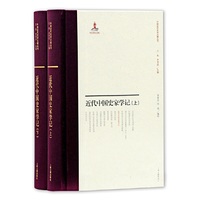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
猜你也喜欢
-
1
¥4.20
-
2
¥22.70
-
3
¥119.20
-
4
¥48.30
新书比价
网站名称
书名
售价
优惠
操作
图书详情
-
出版社
-
ISBN9787532589906
-
作者
-
页数540
-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01日
-
定价¥138.00
-
所属分类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收入了吕振羽、童书业、铁谷等70位近代史学家关于日本汉学的看法和论议,涉及日本汉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学戏曲、书论等诸多面向,对中日文化交流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文章节选
《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
第四篇是“均田成立时代”。此篇以均田制度的发生为着**。以为均田制度的形成有两个经济条件,一是社会生产诸力的破坏(如劳动人口的消减等),一是劳动生产力的向上,社会上具备了前进的条件。同时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又形成自然经济的回转与豪族的发达。其影响到政治组织上便成为“分散的封建制”。过去“**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封建制”至此分解。
第五篇是“官僚主义封建制发展时代”。此篇自隋朝统一直说到明朝灭亡。中唐以前是以均田制度的完成及其废弛为主干,叙述当时土地分配的情形,税法以及村落组织。中唐以后直至明末,是以庄园为主干叙述当时地主与农民生活的情形。本篇之末一章则专论中世的都市与商业。但其中只谈到“市制”、“行会”及“外国贸易”三者。
第六篇是“官僚主义封建的完成及其崩溃时代”。此篇由清初叙至民国初年。以工业生产为主干,叙述中国工业的历史发展、基本形态,以及西欧重商主义破坏中国工商业,致使旧社会崩溃的过程。
森谷克己先生的原书概如上述。*后,我们综合批评他的全书,觉得他能于理论及史料上兼顾并重,以洗中国社会史学家只画图案的弊病,这是他的优点,也正是值得我们介绍的一点。不过,我们对此书也有几处不甚满意。**.《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作者对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的见解,是:殷以前为原始社会,西周为���成熟的封建社会,秦汉以后为官僚主义的封建社会。这种分法是否得当,因为问题过大,本文暂置之不论,只是对于他分析封建社会的方法及名词的运用稍有异议。作者在分析封建社会上过于受字义的束缚。所以对封建社会的着眼点,往往由经济关系上移到政治组织上,更进而视政治组织之变换而更改封建社会的名词。如“官僚主义的封建制”、“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封建制”、“分散封建制”等。这些都可以表示作者着眼点之错误。社会形态的判断,无疑义的是由生产方法及生产关系来决定。封建社会的生产方法的特征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生产关系的特征是实物地租,徭役地租或货币地租(占少量)的剥削关系。因为自然经济占优势,所以封建制度的特点当是非**集权化及土地占有者与土地使用者间的特殊关系。并形成所谓梯形的政治组织。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标识。这些标识往往因为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外来的历史影响等而发生变化。如马克思所谓:“同一经济基础,因为有许多无数量的差异的后人环境——如自然的条件、种族的关系、外来的历史影响等——在它的表现中可以发现出无穷尽的变化和浓淡。”(《资本论》第三卷下册)杜博洛夫斯基也说:“无论大小土地私有者,不管私有者是直接管辖农民,或经过**的官史及警察,不管他是土地私有者,或者只是大领地制度上的土地使用者,不管他是实现他意志的**集权化的**系统,或者他自己直接设立法庭去惩治农民,如果农民经营的是自然经济和家庭工业的联合,并在实物地租的形式上,拿出一部分他自己的生产物交给坐在他上面的土地私有者——剥削者,此种关系就是封建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第四章,吴清友译文)因此,我们对于封建社会,只把握住它的经济基础便够了,大可不必拿政治制度的形态来混乱封建社会的意义。况且,事实上,中国的**集权及官僚制度并不曾移动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在中国社会史中,官僚并不是特殊的**,他们自身大都是封建领主,是构成统治**的一部分,仅仅是为了管理**起见,他们又独自形成一种较严密的组织罢了。在各方面,他们都不曾越过封建的关系,所以没有特别提出来加诸“封建社会”之上的必要。
第二,在论中古封建制度的部分中,作者忽略了大族与官僚的封建领主的地位。他所谓“中古的分散封建制”,只是就魏晋的王侯封君而论。事实上,中古封建社会的本质,不在王侯封君,而在大族官僚等大土地所有者。王侯封君为数甚少,并且他们的收入是国税而不是地租。有时他们竞不得直接与农民发生封建关系。而大族官僚的大地主不但所在多有,并且直接向所属的农奴征收地租或力役。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中间,很显明的保有封建关系。所以论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应以大族官僚的大地主为主体。而森谷克己先生竟对此不提一字。
……
第四篇是“均田成立时代”。此篇以均田制度的发生为着**。以为均田制度的形成有两个经济条件,一是社会生产诸力的破坏(如劳动人口的消减等),一是劳动生产力的向上,社会上具备了前进的条件。同时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又形成自然经济的回转与豪族的发达。其影响到政治组织上便成为“分散的封建制”。过去“**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封建制”至此分解。
第五篇是“官僚主义封建制发展时代”。此篇自隋朝统一直说到明朝灭亡。中唐以前是以均田制度的完成及其废弛为主干,叙述当时土地分配的情形,税法以及村落组织。中唐以后直至明末,是以庄园为主干叙述当时地主与农民生活的情形。本篇之末一章则专论中世的都市与商业。但其中只谈到“市制”、“行会”及“外国贸易”三者。
第六篇是“官僚主义封建的完成及其崩溃时代”。此篇由清初叙至民国初年。以工业生产为主干,叙述中国工业的历史发展、基本形态,以及西欧重商主义破坏中国工商业,致使旧社会崩溃的过程。
森谷克己先生的原书概如上述。*后,我们综合批评他的全书,觉得他能于理论及史料上兼顾并重,以洗中国社会史学家只画图案的弊病,这是他的优点,也正是值得我们介绍的一点。不过,我们对此书也有几处不甚满意。**.《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作者对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的见解,是:殷以前为原始社会,西周为���成熟的封建社会,秦汉以后为官僚主义的封建社会。这种分法是否得当,因为问题过大,本文暂置之不论,只是对于他分析封建社会的方法及名词的运用稍有异议。作者在分析封建社会上过于受字义的束缚。所以对封建社会的着眼点,往往由经济关系上移到政治组织上,更进而视政治组织之变换而更改封建社会的名词。如“官僚主义的封建制”、“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封建制”、“分散封建制”等。这些都可以表示作者着眼点之错误。社会形态的判断,无疑义的是由生产方法及生产关系来决定。封建社会的生产方法的特征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生产关系的特征是实物地租,徭役地租或货币地租(占少量)的剥削关系。因为自然经济占优势,所以封建制度的特点当是非**集权化及土地占有者与土地使用者间的特殊关系。并形成所谓梯形的政治组织。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标识。这些标识往往因为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外来的历史影响等而发生变化。如马克思所谓:“同一经济基础,因为有许多无数量的差异的后人环境——如自然的条件、种族的关系、外来的历史影响等——在它的表现中可以发现出无穷尽的变化和浓淡。”(《资本论》第三卷下册)杜博洛夫斯基也说:“无论大小土地私有者,不管私有者是直接管辖农民,或经过**的官史及警察,不管他是土地私有者,或者只是大领地制度上的土地使用者,不管他是实现他意志的**集权化的**系统,或者他自己直接设立法庭去惩治农民,如果农民经营的是自然经济和家庭工业的联合,并在实物地租的形式上,拿出一部分他自己的生产物交给坐在他上面的土地私有者——剥削者,此种关系就是封建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第四章,吴清友译文)因此,我们对于封建社会,只把握住它的经济基础便够了,大可不必拿政治制度的形态来混乱封建社会的意义。况且,事实上,中国的**集权及官僚制度并不曾移动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在中国社会史中,官僚并不是特殊的**,他们自身大都是封建领主,是构成统治**的一部分,仅仅是为了管理**起见,他们又独自形成一种较严密的组织罢了。在各方面,他们都不曾越过封建的关系,所以没有特别提出来加诸“封建社会”之上的必要。
第二,在论中古封建制度的部分中,作者忽略了大族与官僚的封建领主的地位。他所谓“中古的分散封建制”,只是就魏晋的王侯封君而论。事实上,中古封建社会的本质,不在王侯封君,而在大族官僚等大土地所有者。王侯封君为数甚少,并且他们的收入是国税而不是地租。有时他们竞不得直接与农民发生封建关系。而大族官僚的大地主不但所在多有,并且直接向所属的农奴征收地租或力役。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中间,很显明的保有封建关系。所以论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应以大族官僚的大地主为主体。而森谷克己先生竟对此不提一字。
……
目录
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 吕振羽 评《中国历史教程》 童书业 《东洋古代史》 铁 谷 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评述 刘朝阳 评早川二郎的中国古代社会论 胡瑞梁 评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 陈焕益 读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 曾永潜 介绍《支那社会经济史》(附批评) 忆 恬 《中国社会经济史》 王味辛 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 吴 泽 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 华 岗 李继煌译述的高桑氏《中国文化史》 吴 晗 评《中国文化史》 寿 彝 评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 钱 穆 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 周一良 关于《中国近世史》 李季谷 矢野仁一:《近世支那外交史》 蒋廷黻 《陆奥外交———日清战争之外交史的研究》 王信忠 《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 问 渔 评《东洋历史大辞典》 梁容若 《东洋历史参考图谱》 滋 圃 《东洋读史地图》 禾 子 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研几小录》及《读史丛录》提要 周一良
对于日本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变迁》之辨正 张宏叔 评三宅俊成《中国风俗史略》 张荫麟 《中国秘密社会史》 罗尔纲 《大英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史料》考 谢兴尧 读陈啸仙译新城新藏《东洋文学史大纲》 钱宝琮 《支那法制史研究》 王世杰 《中国建筑史》 仲 中国伦理学史 石 岑
评田崎仁义著《古代支那经济史》 石决明 读田崎仁义著《先秦经济史》后 张国柱 日本稻叶君山牙侩史补正 陈汉章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 陈仲篪 读《元代奴隶考》———奴隶解放九项原因之批评 鞠清远
《中国经学史概说》 睎 读武内义雄《诸子概说》 赵幼文 评《先秦经籍考》 张季同 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底胡译 慧 先 本田成之君《作易年代考》辨正及作易年代重考 靳德峻
《中国文学发凡》 张泽甫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评介 王 岑 介绍日人盐谷温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王栋岑 《中国文学论集》 默 之 日人代庖的《中国文学论集》 一 岳 《南北戏曲源流考》 毓 评盐谷温《元曲概说》 卢 前 批评与介绍: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 陈子展 《中国近世戏曲史》述略 王世琯 关于《中国近世戏曲史》 郑 震 读日本仓石武四郎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研究》 钱南扬 森泰次郎的《作诗法讲话》 赵景深 金泽博士还历纪念《东洋语学之研究》 赦 介绍一本语学的著作:《汉音吴音之研究》(附表) 林春晖 《支那书籍解题(书目书志之部)》 何多源
《中西文化之交流》 维 《日支交涉史话》 钱稻孙 《西域文明史概论》 汪杨时 《西域文明史概论》 汪杨时 《西域文明史概论》的二种译本 于鹤年 《西域之佛教》 梁园东 读白鸟库吉博士《大秦之木难珠与印度之如意珠》(一)一文辨答 章鸿钊 《考证法显传》 汤用彤 《考证法显传》 泉 《张骞西征考》 克 凡 《渤海史考》 毓 《东胡民族考》 克 凡 《燉煌秘籍留真》 周一良 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札记 白寿彝 《蒙古史研究》 克 凡 《蒙古史》 冯承钧 《明初之满洲经略》 酉 生 箭内亘《可敦城考》驳义 唐长孺 《兀良哈及鞑靼考》 梁园东 《满洲发达史》 林同济 《明初之经营东北:驳日人矢野仁一博士谓明东北疆域限于边墙说》刘选民
日本梅原末治博士新著三种 刘厚滋 《东亚考古学论考》(**) 安志敏 《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 青 松 《战国式铜器之研究》 贺昌群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刊行考古书籍四种 伯 平 《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读后记 安志敏 《考古学上より见たる辽之文化?图谱》 何怀德 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 江应梁 《东北亚洲搜访记》 沦 《**次满蒙学述调查研究团报告》 鼎 《内蒙古、长城地带》 青 木 《支那文化史迹》介评 梁绳袆 《长安史迹考》 汤朝华 评杨炼译《长安史迹考》 周一良
对于日本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变迁》之辨正 张宏叔 评三宅俊成《中国风俗史略》 张荫麟 《中国秘密社会史》 罗尔纲 《大英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史料》考 谢兴尧 读陈啸仙译新城新藏《东洋文学史大纲》 钱宝琮 《支那法制史研究》 王世杰 《中国建筑史》 仲 中国伦理学史 石 岑
评田崎仁义著《古代支那经济史》 石决明 读田崎仁义著《先秦经济史》后 张国柱 日本稻叶君山牙侩史补正 陈汉章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 陈仲篪 读《元代奴隶考》———奴隶解放九项原因之批评 鞠清远
《中国经学史概说》 睎 读武内义雄《诸子概说》 赵幼文 评《先秦经籍考》 张季同 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底胡译 慧 先 本田成之君《作易年代考》辨正及作易年代重考 靳德峻
《中国文学发凡》 张泽甫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评介 王 岑 介绍日人盐谷温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王栋岑 《中国文学论集》 默 之 日人代庖的《中国文学论集》 一 岳 《南北戏曲源流考》 毓 评盐谷温《元曲概说》 卢 前 批评与介绍: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 陈子展 《中国近世戏曲史》述略 王世琯 关于《中国近世戏曲史》 郑 震 读日本仓石武四郎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研究》 钱南扬 森泰次郎的《作诗法讲话》 赵景深 金泽博士还历纪念《东洋语学之研究》 赦 介绍一本语学的著作:《汉音吴音之研究》(附表) 林春晖 《支那书籍解题(书目书志之部)》 何多源
《中西文化之交流》 维 《日支交涉史话》 钱稻孙 《西域文明史概论》 汪杨时 《西域文明史概论》 汪杨时 《西域文明史概论》的二种译本 于鹤年 《西域之佛教》 梁园东 读白鸟库吉博士《大秦之木难珠与印度之如意珠》(一)一文辨答 章鸿钊 《考证法显传》 汤用彤 《考证法显传》 泉 《张骞西征考》 克 凡 《渤海史考》 毓 《东胡民族考》 克 凡 《燉煌秘籍留真》 周一良 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札记 白寿彝 《蒙古史研究》 克 凡 《蒙古史》 冯承钧 《明初之满洲经略》 酉 生 箭内亘《可敦城考》驳义 唐长孺 《兀良哈及鞑靼考》 梁园东 《满洲发达史》 林同济 《明初之经营东北:驳日人矢野仁一博士谓明东北疆域限于边墙说》刘选民
日本梅原末治博士新著三种 刘厚滋 《东亚考古学论考》(**) 安志敏 《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 青 松 《战国式铜器之研究》 贺昌群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刊行考古书籍四种 伯 平 《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读后记 安志敏 《考古学上より见たる辽之文化?图谱》 何怀德 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 江应梁 《东北亚洲搜访记》 沦 《**次满蒙学述调查研究团报告》 鼎 《内蒙古、长城地带》 青 木 《支那文化史迹》介评 梁绳袆 《长安史迹考》 汤朝华 评杨炼译《长安史迹考》 周一良
编辑推荐语
适读人群 :供广大读者阅读
《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为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主编之“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之一,由华师大青年**历史学导师贾菁菁编校。《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收入了吕振羽、童书业等70余位近代**史学家关于日本汉学著作的书评或论议,涉及日本汉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学戏曲、书论等诸多面向,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横侧面,对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另有《中国现代史学评论》、《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三种》、《现代大学史学系课程概览》等。
《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为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主编之“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之一,由华师大青年**历史学导师贾菁菁编校。《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收入了吕振羽、童书业等70余位近代**史学家关于日本汉学著作的书评或论议,涉及日本汉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学戏曲、书论等诸多面向,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横侧面,对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另有《中国现代史学评论》、《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三种》、《现代大学史学系课程概览》等。
与描述相符
100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台湾
香港
澳门
海外